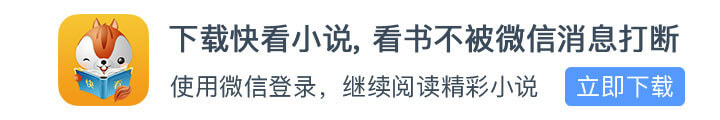第一章
事出有因
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
在我们这些见惯了庄严肃穆场面的中国人看来,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是一点都不神圣的。会议室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席台,没有可以让代表们并排坐在一起的巨型长桌和圆桌,只有一些小型的方桌和靠背椅。桌子的大小,大约只够四个人围在一起吃快餐。这些方桌看上去七零八落,散乱地摆放在会议室里,代表们则三五成群地围而坐之。如果不是因为有一套主席专用的桌椅,你会觉得整个会场更像一个沙龙、酒吧或咖啡厅。坐在这里的代表们也似乎并不是来制定宪法,而是来喝下午茶。[1]
这倒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时的所谓“美利坚合众国”,其实还在草创时期;而所谓“美国人”,则不过是刚刚从大英帝国那里独立出来的那片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他们自由散漫,憎恶霸权,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是连国家和政府都不想要的。他们任命的那些代表,则分属十三个地方性的政治实体。这些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实体之间,就像沙龙里的茶客一样,各自独立,互不相属,原本只有一种松散的联系。他们聚在一起召开会议,同样是迫不得已。如果他们对会议不满,则随时都可以退场,没有人可以阻拦。所以,这种茶座式的会场,对于这样一种会议,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要理解这一点,还必须从美国的建国史说起。
多少读过一点美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北美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国家,只有一些殖民地,其中有一些属于大英帝国,叫“英属殖民地”。不过,英国国王虽然宣称对它们享有主权,实际上却由殖民地人民自己管理,即“主权王有,治权民有”。在1607年到1732年之间,这样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有十六个。后来有三个殖民地被兼并,就只有十三个了。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它们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所谓美利坚合众国,起先就是由这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而成的。
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这些殖民地虽然都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也都号称英属,但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瓜葛。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权力直接来自英国国王的特许。比如弗吉尼亚,就是因为英王詹姆斯一世1606年4月10日颁发的特许状(又称“弗吉尼亚特许状”),由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这一类,叫“公司殖民地”,除弗吉尼亚外,还有马萨诸塞。1620年,在荷兰的部分英国分离派信徒,乘“五月花”号轮船,计划到弗吉尼亚去安家。可是,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六十六天后,到达的不是弗吉尼亚,而是马萨诸塞。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在船上盟誓,要制定对殖民地人民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规则和条例。这个《五月花公约》,就成了第一个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文件;而马萨诸塞,则成为美国独立思想和运动的发源地。
第二类叫“领主殖民地”,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或某些领主的。而且,就像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这类殖民地也可以再分封。比如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就是封给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而巴尔的摩勋爵又分封了六十个庄园。又比如宾夕法尼亚,是因为英王查理二世欠贵族威廉·宾一万六千八百英镑的债,就把北美一大片土地封给宾的儿子小威廉·宾,取名宾夕法尼亚。这类殖民地,数量最多。
第三类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它们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领主,是自由移民根据他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1636年,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在罗杰·威廉斯的带领下,脱离马萨诸塞湾公司,来到罗德岛,按照居民之间自己的约法,建立了一个自治区。后来又和英国签订“宪章”,取得自治。1639年,康涅狄格河畔的一些城镇(哈特福德、温莎、韦瑟斯菲尔德)的居民联合起来签订“基本盟约”,建立了第二个“契约殖民地”,并且和英国签订“宪章”,取得了自治。
很显然,这三类殖民地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即便同一类殖民地,南方和北方也大相径庭。如果既不同类,又一南一北,那差别就更大了。比如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都是靠盟誓或契约来管理的,南卡罗来纳却会把所有的诉讼程序都交给一位“宪兵司令”,佐治亚则连地里种什么庄稼都要由官方说了算。实际上独立战争之前,这十三个殖民地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南北之间更是老死不相往来。
显然,这些殖民地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拢起来。何况大英帝国对它们也一直实行“垂直领导”,并没有在当地设立过统一管理的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它们不像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诸侯一样,上面还有一个“天下共主”。或者说,虽然有,但远在天边。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也是可以互不买账的。1787年的制宪会议开得很艰难,这是原因之一。
这就为它们的联合设置了障碍,也为它们走向共和奠定了基础。但在一开始,它们的联合却是因为迫不得已。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要从英国独立出来,这些原本“不搭界”的殖民地人民很可能会关起门来各自过日子,继续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英国人促成了它们的联合。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五个法令,规定受殖民地人民指控的英国官员只能在英国受审,英国军队可以强行进入殖民地民宅,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等等。
这当然让人无法忍受。对那些具有独立思想和民主意识、视自由为生命的人来说,更是忍无可忍。要知道,许多人之所以远离家乡,来到这蛮荒大陆上做一个乡巴佬,就是为了独立和自由。想想马萨诸塞就知道。1620年,最早的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轮船来到这里时,一共是一百零二人。但仅仅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五十八条生命。可是,第二年春天,当“五月花”号轮船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船长惊诧地发现,居然没有一个人肯和他一起回到“文明”的英国去,而宁愿留在这里做垂死挣扎。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马萨诸塞并不是北美大陆上第一个殖民地(第一个是弗吉尼亚),美国人还是要把乘“五月花”号轮船来到这里的那些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同样,1787年制宪会议在5月30日选举全体委员会时,四十九岁的纳撒尼尔·戈勒姆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主席,也很可能因为他是马萨诸塞人。
总之,尽管这些殖民地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想法,“独立”二字还是把它们联合起来了。1774年9月5日,十二个殖民地(佐治亚缺席)的五十五名代表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会议通过《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那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这种原本有限的反抗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殖民地人民也不含糊,他们决定拿起武器争取自由。1775年4月19日,战争首先在最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马萨诸塞打响(具体地点是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开始了,而且一打就是八年。
其实殖民地人民早就对英国不满了。他们向英国纳税,议会里却没有他们的席位。我们知道,政府是靠纳税人的钱运转的,官员也是由纳税人的钱供养的。英国政府大把地花着北美殖民地纳税人的钱,却不允许他们派出自己的代表,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因此,早在1765年,就有过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这次大会正是那个最不安分守己的马萨诸塞倡议召开的,地点是在纽约,有九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而且,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产生了“美利坚民族”的概念。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新约克郡人。我们都是美利坚人(American)。这下好了,这些英属殖民地人民既然与英格兰或者约克郡不再相干,那就绝不会只是揭竿而起打它一仗就算完事的。
事实上,第二届“大陆会议”还做了三件极其重要的事:一是发表《独立宣言》,二是制定《邦联条例》,三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各殖民地人民制定宪法,并依法建立“能够保护其选民之幸福与安全”的新政府。1776年5月10日,该方案在会上通过。同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次年11月15日,又通过了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负责起草的《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并于1781年3月1日全面生效(马里兰最后一个批准)。这个条例宣布,十三个殖民地将永久性地联合起来,并享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称号——“美利坚合众国”(UnitedStateofAmerica)。
[1]2007年我参观制宪会议会址时,看见了这些方桌和椅子。方桌一共十三张,即每邦(州)一张。罗德岛的一张,恐怕一直是空着的。参观时,有新泽西来的中学生问他们州的代表坐在哪里,讲解员指给他们看了。我问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坐在哪里,讲解员也指给我看了。我又问:宾夕法尼亚有八位代表,四张椅子怎么坐?讲解员没有回答。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在美国的建国史上,有三份文件堪称伟大,这就是《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独立宣言》提出了美国的理想,开始了她的独立;《邦联条例》确定了美国的国名,开始了她的联合;《联邦宪法》则使理想成为现实,使十三个有着各自宪法和政府的政治实体(它们的英文名字是State,如何译为中文回头再说)变成一个完整的实实在在的国家。不过,在1787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之前,很少有人认为还有制定第三份文件(《联邦宪法》)的必要。对于这些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尤其是那些宁愿当乡巴佬也要自由的人来说,什么总统,什么政府,什么首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立宣言》宣布的那个观点: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理想”。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只要产生并说出这个理想,他们就算有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就把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一天(1776年7月4日)定为自己的建国日。何况在《邦联条例》通过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国名。剩下的事情,也就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是英国的承认。这当然只能靠拳头来说话。
所以,1783年9月3日《巴黎和约》签订以后,这些胜利了的乡巴佬,包括那些拿起武器的农民,也包括他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便欢天喜地地一哄而散,解甲归田,回自己的农庄过日子去了。直到四年以后,这些傻乎乎的(或者说天真的)美国人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可不是只有理想就行的。
实际上,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既不像样子,又情况不妙。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许多权力(比如对外宣战、和约缔结、外交主导、货币制造),是由一个一院制的议会来行使的。议会不但身兼立法和行政两职,而且权力很小。比如组建海军、从各州招募军队、解决各州争端等,就至少需要三分之二State的同意。这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成果,无法有效抗衡西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英国人在海上的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实在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之类的重任。原本松散脆弱的联盟(UnitedState),甚至面临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法子,胜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个State,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作“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会议。它的任务,是修改《邦联条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就出在《邦联条例》上。
问题虽然出在《邦联条例》上,但也是有历史原因的。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是美国革命时期的产物,自然存在明显的草创性和过渡性,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是含糊其词甚至含混不清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UnitedStateofAmerica),究竟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盟,还是高度自治地区的联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十三个State就是“州”,美利坚合众国就应该叫做“州联”(事实上也有人主张用这种方式来翻译UnitedState)。相反,如果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则UnitedState就是“国联”,State也得理解为“国家”。可惜“州联”和“国联”都不准确,“合众国”(UnitedState)既不是“州联体”,也不是“联合国”。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交代一遍。
前面讲过,独立战争之前现在叫做“美国”的地方,原本只有一些“殖民地”(Colonie)。1754年的6月,有七个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原因是为了应付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胁。虽说这只是一次临时的动议,却也开始了他们的联合。十一年后,即1765年,又有了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会上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的概念。这就有了一个笼统的“美利坚民族”。等到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时,事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的那些Colonie,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Colonie),一个美利坚人的联合殖民地(UnitedColonieofAmerica)。到1775年至1779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又发生了第二个重大变化。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自己“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则在两年间纷纷效法(马萨诸塞则在1780年6月16日通过新宪法,以取代1776年的旧宪法)。这样一来,原来的Colonie,就变成了具有“半国家”性质的State。这个State应该怎样理解,是一个关键问题。
英文中的State,既可以是国家(比如欧洲国家EuropeanState),也可以是国家的一部分,即“州”(比如德克萨斯州StateofTexa)。可是,在1776年到1787年之间,这些依据《邦联条例》联合起来的State,却既不是国,更不是省,也不是后来联邦制度下的州。为什么不是省呢?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依法成立的政府。唯其如此,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才可以这样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为什么不是国呢?因为它们都没有外交权,国际社会也不承认。独立战争之后,国际社会承认的,是它们的联合体(UnitedStateofAmerica),不是单个的State。所以,这时的State,准确地说是介于国与省(或州)之间的、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
殖民地(Colonie)变成邦(State)以后,原来的“联合殖民地”(UnitedColonie)也就相应地变成了“联合之邦”(UnitedState)。不过UnitedState也可以有两种理解:邦联或联邦。邦联的特点,是各邦拥有独立主权;联邦的特点,则是全国服从统一宪法。那么,1776年到1787年之间的美利坚合众国是邦联呢,还是联邦呢?是邦联。因为这时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宪法,只有条约性质的《邦联条例》。而且,《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这些联合起来的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利”,除非它们同意将其让出。所以,我们只好把这时的UnitedState称为“邦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StateofAmerica),还只是“邦之联合”(邦联),而非“联合之邦”(联邦)。组成“合众国”的那些State,也还只是邦,不是州。但等到《联邦宪法》通过并生效后,State就是州了,不再是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开头部分只好先称其为“政治实体”。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则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说到邦联时,称它为“邦”;在说到联邦时,称它为“州”。这一点,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予以谅解。
但这只是我们今天的说法,当时的美国人是不清楚的。在费城会议上,代表们随意换用邦联(Confederation)和联邦(Union)这两个词,而且一会儿说自己的邦(State)是一个国家(Country),一会儿又用Country指邦联或联邦。可见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正如马萨诸塞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在7月5日的制宪会议上所说,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其实是《独立宣言》留下的老问题。当《独立宣言》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说清楚,这究竟是十三个殖民地组成一个主权国家宣布独立,还是十三个主权国家相邀凑齐了同时宣布独立?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计较这些。那时,最重要的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至于其他,也只能独立以后再说。所以,对许多无法想到或取得一致的问题,只好相互妥协,或者含糊其词,甚至暂付阙如。
这就留下了隐患,带来了麻烦。按照《邦联条例》,各邦基本交出外交权,但可以开展贸易;基本交出军事权,但可以组建军队;基本保留财政权,只有各邦政府才可以直接向居民征税,邦联财政则由各邦按土地价值分摊;基本保留对邦内事务的立法、行政、司法权,交出的权力,则集中于邦联议会。在决定邦联事务时,每个邦各有一票表决权。除非得到九个邦的一致同意,各邦对邦联的授权等于一纸空文。邦联议会休会期间,由邦际委员会代行议会权力。没有一个全国政府,也没有国家元首。这样看来,不但十三个邦(State)具有“半国家”性质,就连所谓“合众国”(UnitedState)也只是一个“半国家”。
这倒是很对那些自由散漫、憎恶霸权的乡巴佬的心思,但可惜难以为继。正如麦迪逊所说,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十三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而要实现全面联合,就必须有一个高于各邦政府的“全国最高政府”,更必须有一部高于各邦宪法的根本大法。这可不是修改一下《邦联条例》就行的。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现在,也只能先把会开起来再说。
费城不是梁山泊
1787年5月25日,修订《邦联条例》的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
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即5月14日,但那天到会的代表却寥寥无几,此后也总是锣齐鼓不齐,驴齐马不齐。一直拖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才有二十九名代表到会。好在这时的美国还是“邦之联合”(邦联),每邦一票表决权。5月25日到会的人刚好可以代表七个邦,过了十三个邦的半数,总算是可以开会了。
不过这里有个细节要啰唆一下,那就是各个邦对代表的授权并不一样。康涅狄格和马里兰规定,只要有一个人出席,就可以代表本邦投票。新罕布什尔、纽约、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规定至少两人,马萨诸塞、新泽西、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规定至少三人,宾夕法尼亚要求最严,规定至少四人。巧得很,5月25日,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刚好是四个人(罗伯特·莫里斯、托马斯·菲茨西蒙斯、詹姆斯·威尔逊、古弗尼尔·莫里斯),到28日又来了四个(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克莱默、托马斯·米夫林、贾里德·英格索尔),更是阵容强大。宾夕法尼亚在这次制宪会议上举足轻重,作用很大,其代表差不多也都是一时之选(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到)。宾夕法尼亚代表达到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就有了希望。
至少需要三名代表的新泽西也刚好来了三人:戴维·布瑞利、丘吉尔·豪斯顿、威廉·佩特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十二岁的威廉·佩特森。我们知道,1787年的费城会议实际上是各邦各派政治力量逐鹿中原折冲樽俎的战场,而在第一回合和主流方案进行斗争的“首席剑客”,就是这位佩特森先生。请读者记住他的名字,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说到他。
佩特森的盟友是四十三岁的冈宁·贝德福德。他是特拉华代表,也是“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新泽西学院的同学和室友。不过,他在会上却和麦迪逊唱对台戏,曾指名道姓痛斥麦迪逊等人“兴妖作怪”。冈宁·贝德福德是在28日到会的。25日前,特拉华代表团已有三人到会:乔治·里德、理查德·巴塞特、雅各布·布朗。其中,里德是最先向主流方案发起挑战的人,只不过他出手没有佩特森那么重。
北卡罗来纳超额,四人(亚历山大·马丁、威廉·理查森·戴维、理查德·多布斯·斯佩特、威廉森)。需要两名代表的南卡罗来纳也超额,也是四人(约翰·拉特利奇、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查尔斯·平克尼、皮尔斯·巴特勒)。纽约则刚好两人(罗伯特·耶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纽约这两位代表都很重要。汉密尔顿作为华盛顿的密友和联邦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参加制宪会议时只有三十二岁。在制宪会议上,他发言不多,但作用不小,而且也提出了自己的制宪方案(即《汉密尔顿方案》),是会议的第四种方案(还有一种是南卡罗来纳代表查尔斯·平克尼提出的,即《平克尼方案》)。罗伯特·耶茨三十九岁,在制宪会议上没有发言,却和约翰·兰辛(6月2日到会)联手,在纽约代表团内以二比一压倒汉密尔顿,成为会上有名的反对派。后来他们发现,即便留在会上坚持反对意见,也无法扭转乾坤,便于7月10日一同离去,留下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汉密尔顿徒唤奈何。不过汉密尔顿虽然在制宪会议上处境尴尬,少有作为,但他的理想——建立一个由富人控制的金融工商业社会,却最终成为美国的现实。
马萨诸塞只有一人(鲁弗斯·金),人数不够(到28日才又来了两人:纳撒尼尔·戈勒姆、凯莱布·斯特朗)。佐治亚也只有一人(威廉·菲尤),人数也不够。康涅狄格没有来人(28日来了一人:奥利弗·埃尔斯沃思),马里兰没有来人(28日来了一人:詹姆斯·麦克亨利),新罕布什尔掏不起路费,代表无法启程(两个月后才自掏腰包赶了过来),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算下来,到5月25日,以上有法定代表权的邦是六个。加上弗吉尼亚代表团全部到齐,就有了七个有表决权的邦。当然,因为直到这天才好歹凑够七个邦,正式会议也就因此而延期了十一天。
这就很有些出师不利的味道,实际上这次会议也开得很艰难。正式代表七十四人,最后实到只有五十五人,而且会议开始以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十三人,坚持到底的只有四十二人;而这四十二人中,又有三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便只有十二个邦的三十九名代表。其中汉密尔顿还没有表决权,只能以个人名义签字,不能代表他的邦。所以,在宪法上签字的,准确地说是十一个邦。
不过会议好歹总算是开起来了。继5月25日到会二十七人后,28日又到九人。而且,因为康涅狄格和马里兰各有一人到会,马萨诸塞增加了两名代表,有表决权的邦就有十个了。28日到会的代表中,有一位奥利弗·埃尔斯沃思先生必须特别加以注意。四十二岁的埃尔斯沃思是康涅狄格代表。正是他,一方面抵制了麦迪逊等人中央集权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和本邦其他代表一起促成了大邦和小邦之间“伟大的妥协”,使差一点夭折的会议起死回生。这个故事,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细说。
5月29日,特拉华的约翰·迪金森和马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到会。这是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五十五岁的约翰·迪金森是美国独立运动初期的精神领袖,也是这次会议要修订的《邦联条例》的起草委员会主席。四十三岁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则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二十八岁就当选马萨诸塞议会议员,追随塞缪尔·亚当斯争取独立,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他们的到会,增加了会议的分量。
以后又有人陆续来到会场。5月30日,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到会。六十六岁的罗杰·舍曼是老资格的革命领袖,参加过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是《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的起草委员会委员。他也是这次会议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制宪会议在议会席位问题上的僵局,就是他和同一个邦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一起设法打破的。当然,在会议前期,他也没少和麦迪逊他们唱反调。
5月31日,佐治亚的威廉·皮尔斯到会。他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份《制宪会议代表性格描述》。6月1日,佐治亚的威廉·胡斯顿到会,他后来在7月2日的会议上投下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票”,使表决结果出现五邦赞成,五邦反对,一邦赞成反对各半的局面。这次表决惊险之极,差一点就断送了美国的前程,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这里要说的是,由于威廉·胡斯顿到会,佐治亚有了表决权。可惜,马里兰的詹姆斯·麦克亨利刚好在第二天离会,所以第二天有表决权的邦还是十个。
6月2日,康涅狄格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马里兰的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纽约的约翰·兰辛到会。六十岁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是哥伦比亚学院的第一任校长。独立战争后,他成为邦联议会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约翰·兰辛的情况前面说过了,而六十四岁的托马斯·杰尼弗·丹尼尔的到来,则延续了马里兰的表决权,使有表决权的邦恢复到十一个。不过,这位杰尼弗·丹尼尔先生的观点总是和6月9日到会的路德·马丁相左,结果总是出现“马里兰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的尴尬局面。
6月5日,六十四岁的新泽西行政长官威廉·利文斯顿到会。6月9日,自始至终的反对派、马里兰代表路德·马丁到会。6月11日,佐治亚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到会。6月20日,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到会。6月21日,制宪会议中最年轻的代表(二十七岁),新泽西的乔纳森·戴顿到会。7月9日,马里兰的丹尼尔·卡罗尔(五十七岁)到会。他一来,马里兰的代表就从两个变成了三个,“马里兰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的局面就终止了。
7月23日,新罕布什尔的约翰·兰登和尼古拉斯·吉尔曼到会。他们能来,全靠四十六岁的约翰·兰登先生慷慨解囊,自掏腰包支付两人的路费,新罕布什尔总算没有缺席。兰辛和耶茨7月10日离会后,纽约代表团失去表决权。新罕布什尔代表团的到来,使有表决权的邦恢复到十一个。
8月6日,马里兰的约翰·弗朗西斯·默瑟到会。这是最后一位到会的代表,而且几乎一到(8月8日)就表示对整个方案的反感,断言方案绝不可能成功。在做了大约十八次发言后,他在8月17日或者18日离开会议,而且一去不复返。他的到会,好像只是为了表示反对。和他一样以退场表示抵制的代表一共有四个。两个是纽约的,即耶茨和兰辛;两个是马里兰的,即路德·马丁和默瑟。不过默瑟到会时间短,耶茨并不发言,舌战群儒的主要是兰辛和路德·马丁。其中战斗力最强的又是路德·马丁,他一直战斗到9月4日才退场。
我写这一段文字,感觉就像是在读《水浒》,一会儿一拨好汉上山,一会儿一拨好汉上山。可惜费城不是梁山泊,会议代表也不是江湖好汉。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一样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也不会但有动静便齐声唱道:“头领哥哥说的是。”相反,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也为了各邦利益、个人观点,他们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旷日持久难解难分的大辩论,使唇枪舌剑的会场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
光荣与权力
5月25日的会议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选举五十五岁的弗吉尼亚代表、前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为大会主席。
乔治·华盛顿的名字,我们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在我们看来,由他担任大会主席,实在是当之无愧。事实上这项提议也得到了七个代表团的一致赞同,华盛顿全票当选。但我们还是要指出,这项提名仍然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因为它来自宾夕法尼亚代表团,而且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提议、罗伯特·莫里斯提名的。
宾夕法尼亚是仅次于弗吉尼亚的第二大邦,人口居第二,土地面积第五。它的代表团也阵容强大,人数最多,一共八人(次为弗吉尼亚,七人),其中至少有四人相当重要:罗伯特·莫里斯、古弗尼尔·莫里斯、詹姆斯·威尔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五十三岁的罗伯特·莫里斯是在《独立宣言》《邦联条例》和《联邦宪法》这三份堪称伟大的文件上都签过字的人。这样的人一共只有两个,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是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三十五岁的古弗尼尔·莫里斯是制宪会议期间发言次数最多的代表,共发言一百七十三次。而且,由于他文笔精巧细腻,宪法文本最后主要是由他来定稿的。四十五岁的詹姆斯·威尔逊发言次数位居第二,一百六十多次(再次为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一百五十多次),而且他的许多具体建议成为《弗吉尼亚方案》的血肉,最后被纳入联邦宪法。如果以发言次数来做排行榜,则冠军和亚军便都在宾夕法尼亚代表团。何况这两个发言最多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古弗尼尔·莫里斯是世家子弟,本人则“集种种才华于一身”,发言口若悬河,汪洋恣肆。詹姆斯·威尔逊是当时美国立宪问题的专家,对世界上各种政体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也是联邦宪法生效后首批任命的最高法院六名大法官之一。制宪会议代表中后来当了大法官的共有三人。一个是他(1789年任命),还有一个是新泽西的威廉·佩特森(1793年任命),康涅狄格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则是第三任首席大法官(1796年任命)。后来当了总统的则有两人,即华盛顿和麦迪逊。这两个都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是两个分量最重的邦。
实际上这次会议也是由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主导的。这两个代表团的意见,代表着会议的主流方向。由宾夕法尼亚代表团提名弗吉尼亚人担任大会主席,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何况这个提名又其实来自本杰明·富兰克林。
这又是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姓名。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他在暴风雨中放风筝以证明雷电不是上帝发怒的故事,知道他发明了避雷针,知道他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比如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科普利奖章、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荣誉学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法兰西科学院的外国院士、彼得堡科学院的外国院士等)。我们还知道他由于家境贫寒,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当了印刷工。靠着刻苦自学和勤奋努力,他不但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还在费城创办了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创办了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们当然还知道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政治家,更是启蒙思想家。第一个把北美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的“1754年阿尔巴尼计划”,就是他提出来的。他也是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和《独立宣言》的起草委员之一,并曾远涉重洋出使法国,赢得了法国和欧洲人民对北美独立战争的支援。这次来参加制宪会议时,他是宾夕法尼亚的行政长官。富兰克林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被历史学家称为“美国先生”和“最美国的美国人”。1790年去世时,费城人民为他服丧一个月以示哀悼,出殡队伍竟达两万人之多。尽管他的墓碑上只刻着“印刷工富兰克林”几个字,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却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赞语:“他从苍天那里取得了雷电,从暴君那里取得了民权。”
这样一个人,如果用“德高望重”四个字来形容,那可真是恰如其分。何况他参加制宪会议时已八十一岁,是会议中真正的元老和长者。如果提名他当主席,恐怕也会全票当选。实际上,联邦宪法最后得以通过,富兰克林和华盛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华盛顿的威望给人以信心,富兰克林的智慧给人以启迪,而他们两人的高风亮节,则更是起到一种楷模的作用。富兰克林提名华盛顿当主席,实在是为会议开了一个好头。
罗伯特·莫里斯提名后,南卡罗来纳代表约翰·拉特利奇附议。四十八岁的约翰·拉特利奇也是一个“老革命”,参加过1765年的“反印花税法大会”和两届大陆会议。拉特利奇附议后,进行了书面投票,七个邦七票赞成。于是罗伯特·莫里斯和约翰·拉特利奇便引导华盛顿在主席座位上就座。华盛顿向与会代表郑重道谢,感谢大家授予他如此殊荣。他提醒代表,他对自己将要履行的任务深感惶恐,倘有不到之处,希望会议能够予以宽容。
实际上华盛顿在整个会议期间都表现得十分谦虚、谨慎和低调。5月29日,大会决定采取全体委员会的形式,讨论邦联现状和弗吉尼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邦联条例》的方案(即《弗吉尼亚方案》)。5月30日,大会选举马萨诸塞的纳撒尼尔·戈勒姆担任全体委员会主席。此后,华盛顿便只在每天开会和散会时上台就主席座,作为会议开始和结束时的礼仪。其他时间,他都坐在弗吉尼亚代表团的桌子旁,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讨论和投票。他在会上一共发言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一天,当选主席后致简短答谢词。第三次是在最后一天,问由他保存的会议记录以后怎么办。第二次也是在最后一天,对戈勒姆的一项动议表示附议。在这唯一一次实质性的发言中,华盛顿说,他的处境限制了他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情绪。但现在已到最后关头,大家都希望这个方案遭到的反对越少越好。因此,他认为应该采纳刚才这个建议。华盛顿一言九鼎,戈勒姆的动议被一致通过。
华盛顿在会上的这种低调,有表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他成为合众国的缔造者(Father),则既因为他“有所为”,更因为他“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自然是指他领导了独立战争,参加了制宪会议,担任了合众国第一届总统。所谓“有所不为”,则是指他作为手握兵权的总司令,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把军权交还给国会;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票当选的总统,在行将结束第二届总统任期之际,郑重向全国人民表明退休还乡的愿望,开创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华盛顿有所为,美利坚民族得以独立;华盛顿有所不为,美利坚人民不受其害。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他成为合众国的Father。Father这个词,除“父亲”外,还有“创立者”和“缔造者”之意。过去我们都称华盛顿为美国的“国父”,其实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事实。把“合众国的缔造者”(或“创立者”)理解为“国父”,是一种典型的帝制思维和专制思维(称皇帝为“君父”)。华盛顿却并不认为他是美利坚人民的父亲,而只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作为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甚至还有点平庸的人。他在青年时代既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也没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概,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更多的土地,在英国殖民常备军谋个一官半职。如果不是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他也许会在他弗吉尼亚的农场里了此一生。他的智力并无多少超人之处,形象也没有什么特殊魅力。他文笔流畅但缺乏文采,待人诚恳但刻板冷淡,和他共进晚餐竟如“葬礼般的肃穆”。历史和人民选中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人品。他的诚信无懈可击,他的公正自始至终,他的良心使他的决策丝毫不受个人利害、亲缘、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何况他还有与诚信、公正和良心密切相连的另一种美德——审慎。这就使大家相信,把国家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面对突如其来蜂拥而至的崇拜和荣誉,华盛顿感到诚惶诚恐并一再萌生退意。在交出了手中的“克敌制胜之剑”,回到弗农山庄务农后,他非常不愿意重入政坛。这种想法使他在1789年接受总统职位时,竟然抱着像“一个死刑犯步入刑场”一样的心情。这次制宪会议,他原本也是不想参加的。只是在各方的一再请求下,他才同意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勉为其难。这是他在会上三缄其口的深层原因。当然,作为主席,过多地表态会影响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人品高尚且非常自律的华盛顿当然知道这一点。
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华盛顿在会上是无所作为的,更不意味着他对于这次会议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制宪会议之前,他就曾与“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互通信息,共商建国制宪的大政方针。麦迪逊则把自己草拟的新制度大纲给华盛顿过目。因此有人认为,新宪法和制宪会议实际上是华盛顿和麦迪逊密谋的产物。华盛顿虽然并不愿意亲自出席会议,但一旦参加,则投之以全身心。何况如果没有他作为美利坚民族团结的象征坐在会场,这次会议弄不好真会一哄而散。相反,由于他的出席并担任主席,制宪会议的目的便和美国革命的主题联系起来了。这是会议的精神基础。在后面的描述中我们将看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那一轮红日才终于能够喷薄而出。
关注官方公众号,方便下次阅读

微信内长按三秒关注
建议您关注公众号,以免下次找不到当前小说
1、如果在微信内浏览,请直接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关注公众号,以免下次找不到当前小说。
2、进入公众号后,点击左下方菜单“看过的书” 进入 “阅读记录” 即可阅读本书。